古蜀國
發(fa)布日期:2016-09-13 13:47:09 訪問(wen)次數:1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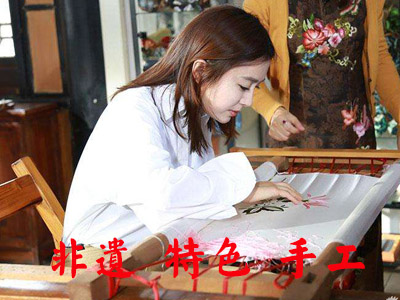
考古(gu)工(gong)作者們在對金沙遺址的第六次發掘。當天就出土了130多件珍貴文物,在這些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發現了中國迄今為止最大的商代石磬。
此次共發掘了兩個商代石磬。其中最長的一個長達1.1米,堪稱中國目前發現的最大的商代石磬;在它的旁邊還躺著一個約四五十厘米的稍小的石磬,兩個石磬都可以找到一個小孔。在清理中,工作人員還發現其中的一個石磬上還刻劃著清晰的弦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介紹,這個石磬的發現非常意外,他當時就在現場,還是他第一個喊出了石磬的名字,這個發現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很激動。
磬是當時的廟堂之音,也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樂器。它是古蜀王在祭祀時用來演奏的樂器,據專家介紹,這種樂器在四川地區屬首次發現。它的發現真實地反映了古蜀王祭祀時的場景。同時也證明了金沙時期的祭祀活動中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禮樂制度。
不論金沙遺址出土的石磬、太陽神鳥、玉璋還是玉琮無不彰顯出當時社會的高度文明。可是人們仍然不明白,為什么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國會有如此高的文明,是什么造就了它的發展?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孫華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四川成都平原屬盆地地區,周邊較高的地區當時很可能有著很高的文化。成都平原又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溫暖濕潤,雨量充沛,而且有很多的河流。當時茂密的叢林很適宜人類生存繁衍。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四周的居民開始慢慢向這里聚集,來自不同的地域的人,也帶來了不同的技術和藝術,各方文化在這里匯集,這里成了中國西南地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之一。
謎團二:成都平原的良渚、三星堆、金沙遺址究竟如何傳承?
在金沙遺址的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對發掘出來的器物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從出土的這些器物的形制上看很多都與據金沙村大約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帶和青銅小立人,都驚人的相似。
孫華介紹,金沙出土的青銅小立人僅有19.6厘米,這是金沙遺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銅器。它與三星堆出土的2米高的青銅大立人在造型方面極其相似,身上都穿著同樣的長衣,擺出同樣的姿態,一只手空空地攥著拳頭。不同的僅僅是身高上的懸殊,但從金沙青銅小立人下面的一個小插件可以看出,它此前應該是插在一個大件上的一個物品。除身高的不同,形制上看,兩個青銅立人所差無幾。
金沙遺址中出土了金冠帶上面刻有魚、鳥、箭、人頭圖案,其做工也很精致。更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圖案與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圖案完全一致。孫華認為,金冠帶與金杖都是至高王權與族權的體現和代表,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紋飾具有相同的象征意義,反映出了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之間內在的緊密聯系。
的突然消失,給人們留下了很多待解的謎團。有猜測說:“三星堆的消失可能是外族的入侵。”還有猜測認為是受到洪水的侵襲,族人全部外遷所致。所有這些都是人們的猜測。金沙遺址的發現似乎可以解開一些三星堆突然消失之謎。
此外,金沙出土的22厘米的青玉琮在眾多的玉琮中顯得尤為突出,它的顏色為翡翠綠,雕工極其精細,表面有細若發絲的微刻花紋和一人形圖案,上面的微雕圖案令人叫絕,堪稱國寶。
整個玉琮分為十節,玉琮上雕刻有40個人面紋和一人形圖案,人體肥胖,頭上戴有一個冠飾,雙臂平舉,兩臂上都有一個上卷的羽毛形裝飾,雙腳叉開,長袖飄逸。整個玉器為青色,玉質非常溫潤,呈半透明狀。從造型風格看與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謝輝在談到對金沙遺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幾點認識的時候曾表示,金沙遺址青玉琮與良渚文化的玉琮仔細研究發現二者之間仍存在一些差異:首先質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為雞骨白,金沙遺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風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還沒有發現青玉琮的造像風格的圖案。
謎團三:如此高的文明為何沒有文字?
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顯示出了當時精湛的工藝,可是這種高度的文明到目前為止仍沒能找到任何的文字,難道當時沒有文字?
王仁湘說:“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并非沒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證明。”在殷墟甲骨文沒有被發現之前,人們并不知道商周有文字存在。在殷墟出土的龜甲、獸骨上可以發現,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貴族在龜甲、獸骨等占卜材料上記錄了大量的與占卜有關事項的文字,也包括少數刻在甲骨上的記事文字。這個時候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商周不僅有文字,而且相當的成熟。
雖然目前金沙遺址中發現的卜甲上并沒有發現任何的文字,但不代表這里沒有文字存在,我們現在挖掘的僅是金沙遺址的冰山一角,還有更多有價值的金沙文化有待進一步的發掘,文字并不一定都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他的可以刻字的材質上。沒有發現并不代表沒有,將來的情形還不好說,現在還不能下定論。還有可能是因為保存的關系,流失了很多。比如有可能把文字刻在樹葉或者是樹木上,雖然現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刻在卜甲、銅器上的,但不能認為只有卜甲或者銅器上才會有這樣的文字。
孫華認為,有沒有文字有不同的說法。按照文獻的說法,確實沒有文字記載。此前有一種說法,一個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國著書立說,如果當時沒有文字的話就不可能會有這樣的說法。但是,這種說法目前還沒有得到證實。
在四川也沒有發現像楚國那樣的帛書、竹簡這些文物,但在四川商代晚期,還是可能有文字的,那時流傳著一種“巴蜀符號”,但這種符號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還沒有定論
歷史
作者:何小顏, 筆名那父,男。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副編審。
據文獻記載, 古蜀國最早的先王是蠶叢、柏濩 ( 伯灌)、魚鳧, 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鱉靈, 或說是蒲澤, 其后是開明。① 這些帝王名號怪異, 史料匱乏, 正如詩人李白喟嘆道:“蠶叢及魚鳧, 開國何茫然”, 長久以來, 其歷史一直是云遮霧罩, 成為困擾著人們的難解之謎。
可資留意的是,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一段看似荒誕的文字, 對揭示蜀國開國之秘有重要幫助:
有魚偏枯, 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為魚, 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這里的關鍵詞“魚婦”, 學界向無確詁。有人以為指上身為婦人、下身為魚的“魚美人”, 其實不然。按,“魚婦”即蜀先王魚鳧的別寫;“蛇乃化為魚”, 則隱含了民族融合、圖騰易幟的劇烈變故。其理由可先從文中的顓頊說起。
顓頊是五帝之一。在神話系統中, 他是水神, 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鯀的父親、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說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鯀, 鯀生禹, 禹生啟。②作為他的子裔, 鯀、禹同樣具有水族的特征。他們都有魚的化身。③《山海經·大荒北經》說:“西北海外, 流沙之東, 有國曰中車扁, 顓頊之子。” 這里“中車扁”, 和上面《大荒西經》講的有魚“偏枯”, 是一個意思。這個顓頊之子, 顯然指鯀。鯀,又作鮌, 即玄魚。④《莊子·盜跖》說:“禹, 偏枯。”《列子·楊朱》說:“大禹,一體偏枯。”禹也是魚, 而且禹、魚是同音通假字。魚的形象其實就是該族團的圖騰, 它可以上溯到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遺址大量出土的魚圖騰徽志。
如上所說,《山海經》“有魚偏枯, 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這段話的內在聯系已清楚了, 但作為沿襲魚圖騰的顓頊一脈與蜀先王魚鳧之間的關系, 還值得進步討論。
巴蜀在中國古代地理觀念中, 是西部的大本營之一( 另一個是以西王母為神性代表的昆侖山, 確切地點不明, 有的說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證明顓頊族團所處的西方具體位置恰恰就在巴蜀。
有叔歜國, 顓頊之子。
——《山海經·大荒北經》
有國名淑士, 顓頊之子。
——《山海經·大荒西經》
顓頊母, 濁山氏之子, 名昌仆。
——《世本》
歜、濁、淑、叔, 皆為蜀字的異寫。濁山氏, 《十三州志》徑寫作蜀山氏:“蜀之先, 肇于人皇之際, 至黃帝昌意(昌仆)娶蜀山氏女, 生帝嚳, 后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 始稱王者。”只是所生者為帝嚳, 因此有學者認為, 帝嚳就是顓頊。再看下面:
帝顓頊生自若水, 實處空桑, 乃登為帝, 惟天之合。
——《竹書紀年》.
若水, 古水名, 在今四川省。 那么, 顓頊竟是巴蜀人, 或至少顓頊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山海經·海內經》曾列出一個著名的巴蜀帝系, 說是“西南有巴國, 大嗥生咸鳥, 咸鳥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為人。” 顓頊又號高陽, 高陽與太昊(大嗥)族關系密切。因此, 和這個譜系也對得攏。不同的是, 太昊風姓, 屬東夷集團, 以鳳鳥為圖騰。但這正說明顓頊這一集團族氏成分的復雜性。
鯀也生于西方。《吳越春秋·越王無馀外傳》:“鯀……家于西羌。”關于禹,證據更多。《新語·術事》:“大禹出于西羌。”《史記·六國年表》:“故禹興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語:“禹生石紐, 西夷人也。”《太平御覽》卷八二引《帝王世紀》:“伯禹……長于西羌, 夷人。”而《史記·夏本紀》正義引《蜀王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更指明禹為今四川汶山縣人。
羅列這些資料, 并不意味要否定黃帝、顓頊、鯀、禹、啟這一大系發祥于中原腹地并構成了華夏文明的歷史主脈。上面的引證與其他史料相對照, 存在不少矛盾沖突的說法, 例如, 有關顓頊的活動區, 《左傳》等書就有陳、衛等地( 今屬河南一帶) 的記載。這一現象表明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黃帝族裔的發展是復雜的, 它經歷了各民族血緣和文化的大融合。
近年來廣漢三星堆遺址的發掘, 表明巴蜀自有其迥異于中原的文化淵源, 這可證實巴蜀原住民的土著性質。其文明( 距今5000~3000年) 的匆匆消失, 不排除是中原文明楔入的結果。
我以為《山海經·大荒西經》那段話, 曲折地透露了巴蜀被納入華夏文化圈的信息。
大荒西部, “有魚偏枯, 名曰魚婦”。魚婦, 即魚鳧, 婦、鳧同音通假。“有魚偏枯”, 這是表征顓頊、鯀、禹族團特有的用語, 說明魚鳧與顓頊族團有非同尋常的關聯。這兩句開宗明義, 魚鳧是以魚為圖騰的族團或朝代。
“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為魚, 是為魚婦”, 則展現了民族融合的的殘酷和激烈。在中原有過漫長發展階段的顓頊族團, 在巴蜀早有落腳之點, 其勢力在擴張中與巴蜀土著發生了尖銳的沖突, 終于, 在洪水( 大水泉) 爆發的歲月里, 雙方出現了正面交鋒。在后來的兼并戰爭中, 魚圖騰取代了蟲圖騰( 蜀蠶、巴蛇等), 但顓頊也在這場消耗戰中元氣大傷, 于是“顓頊死即復蘇”, 進入了鯀的時代。這個鯀, 號魚婦, 史稱“魚鳧”。
這便是古蜀國由“蛇乃化為魚”的歷史真相。從此揭開了魚族世家在巴蜀治國理水的英雄篇章。
猶如魚鳧可與鯀對應一樣, 蜀先王鱉靈、開明也可與禹、啟一一對應。
.鯀死為鱉靈, 復活后即是禹。《國語·晉語》、《吳越春秋·越王無馀外傳》都說鯀死化為黃 ( 能) 即三足鱉, ⑤也即是鱉靈。《水經注·江水》卷三十三引《本蜀論》:“荊人鱉令( 靈) 死, 其尸隨水上, 荊人求之不得也。令( 靈) 至汶山下, 復生, 起見望帝。……望帝立為相。”鱉靈本是鯀尸, 再生, 應即是禹, 其神格、事功與禹契合。“復生”, 又可訓讀為“腹生”。《山海經·海內經》曰:“鯀復生禹。”《楚辭·天問》曰:“伯鯀腹禹。”皆為“腹中生出”之意。故《初學記》二二引《歸藏·啟筮》有此神話:“鯀殛死, 三歲不腐, 付之以吳刀, 是用出禹。”注意前述鱉令( 靈) 至汶山下復生的文字, 與禹為四川汶山縣人相合, 亦證明鱉靈即禹, 應是同格帝王。
蜀帝開明同夏后開, 即啟。啟改開, 因漢代人避景帝劉啟諱而改。
筆者認為, 自魚鳧(鯀)而下, 巴蜀歷史明顯地帶有了中原文明的投影, 其交疊重復, 反映了巴蜀已經喪失其獨立性, 而水乳交融加入到中華文化圈中了。
————————————————————————
①《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蜀王本紀》作蠶叢、柏濩、魚鳧、杜宇、鱉靈(開明)、盧保(開明)。《漢唐地理書鈔》引《蜀王本紀》作蠶從、伯灌、魚鳧、蒲澤、開明。
②見《大戴禮·帝系》、《史記·五爺本紀》、《世本·帝系篇》、《竹書紀年》、《隨巢子》等。
③水神有魚的形象, 又可見《酉陽雜俎·諾皋記上》所說的河伯:“河伯……人面魚身。”
④《太平御覽》卷九三六引《拾遺錄》:“夏鯀治水無功, 沉于羽淵, 化為玄魚。……后世圣人以魚為神化之物,以玄字合于魚為鯀字。”
⑤《爾雅(ya)·釋魚》:“鱉三(san)足,�������� 能。”束皙《發(fa)蒙記》:“鱉三(san)足�����曰 。”

